贸易战6年多,美国越打越“亏”陷泥潭,中国苦练“内功”正当时
贸易战6年多,美国越打越“亏”陷泥潭,中国苦练“内功”正当时
贸易战6年多,美国越打越“亏”陷泥潭,中国苦练“内功”正当时近年来(jìnniánlái),美国打着减少贸易逆差、重振制造业的旗号,发起对华贸易战,然而事与愿违,逆差不降反升,制造业就业不增反减,且导致国内通胀高企,全球供应链(gōngyìngliàn)紊乱。在中美博弈将长期持续的背景下,面对技术封锁和外需疲软(píruǎn)等挑战,中国需完善(wánshàn)创新体系,优化研发(yánfā)资源配置,同时改革收入(shōurù)分配、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,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,进而缓解通缩压力,推动经济向更包容(bāoróng)、均衡、可持续的方向转型。
本文为中国观察智库独家(dújiā)约稿,转载请注明来源:中国日报(zhōngguórìbào)中国观察智库。
 作者:万广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席教授(jiàoshòu),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(yuànzhǎng)
2018年(nián)(nián)(nián)3月22日,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,当时(shí)特朗普(tèlǎngpǔ)政府的官方理由是要减少贸易逆差。然而事与愿违,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2017年特朗普上台前为3752亿美元,到2022年特朗普下台时不降反升,达到3829亿美元。更尴尬的是,贸易战打了(le)6年多,把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从2017年的5660亿美元打到了2024年的9184亿美元。
美国政府(měiguózhèngfǔ)还声称,加征关税是为了推动制造业回流和(hé)增加就业,但这些目标也未实现(shíxiàn):2022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为1298万人,目前降至1280万人。不仅如此,关税还推高(tuīgāo)了美国的(de)通胀水平,2025年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(CPI) 同比增长2.3%,环比增长0.2%,对消费者和下游(xiàyóu)企业构成负担。同时,加征关税破坏了全球供应链,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。
加征关税和贸易战(màoyìzhàn)都是“逆(nì)全球化”浪潮的(de)一部分。特朗普借助“逆全球化”等民粹议题赢得了2016年(nián)和2024年两届总统选举,表明(biǎomíng)其政治基础并非短期现象。从结构性因素看,只要全球化红利无法在国内实现公平分配,类似贸易战的政治工具就将不断被使用,成为某些国家内部矛盾外溢的主要出口。
事实上,过去几十年来,美国(měiguó)的投资者、跨国公司和高收入群体从全球化中获益巨大,但低收入群体和中产阶级获益甚微。比如(bǐrú),从1990年到2023年的长达30多(duō)年间,美国经济(jīngjì)年增长率一直维持在2%-2.5%,但美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率仅为(wèi)0.5%,几乎可以忽略。贫富差距的扩大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重要推动力,也为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提供(tígōng)了土壤。
作者:万广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席教授(jiàoshòu),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(yuànzhǎng)
2018年(nián)(nián)(nián)3月22日,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,当时(shí)特朗普(tèlǎngpǔ)政府的官方理由是要减少贸易逆差。然而事与愿违,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2017年特朗普上台前为3752亿美元,到2022年特朗普下台时不降反升,达到3829亿美元。更尴尬的是,贸易战打了(le)6年多,把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从2017年的5660亿美元打到了2024年的9184亿美元。
美国政府(měiguózhèngfǔ)还声称,加征关税是为了推动制造业回流和(hé)增加就业,但这些目标也未实现(shíxiàn):2022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为1298万人,目前降至1280万人。不仅如此,关税还推高(tuīgāo)了美国的(de)通胀水平,2025年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(CPI) 同比增长2.3%,环比增长0.2%,对消费者和下游(xiàyóu)企业构成负担。同时,加征关税破坏了全球供应链,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。
加征关税和贸易战(màoyìzhàn)都是“逆(nì)全球化”浪潮的(de)一部分。特朗普借助“逆全球化”等民粹议题赢得了2016年(nián)和2024年两届总统选举,表明(biǎomíng)其政治基础并非短期现象。从结构性因素看,只要全球化红利无法在国内实现公平分配,类似贸易战的政治工具就将不断被使用,成为某些国家内部矛盾外溢的主要出口。
事实上,过去几十年来,美国(měiguó)的投资者、跨国公司和高收入群体从全球化中获益巨大,但低收入群体和中产阶级获益甚微。比如(bǐrú),从1990年到2023年的长达30多(duō)年间,美国经济(jīngjì)年增长率一直维持在2%-2.5%,但美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率仅为(wèi)0.5%,几乎可以忽略。贫富差距的扩大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重要推动力,也为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提供(tígōng)了土壤。
 尽管特朗普发起(fāqǐ)的贸易战具有(jùyǒu)(jùyǒu)个人决策的偶然性,但中美冲突则具有明显的历史必然性。一方面,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,原有的分工格局和收益分配机制受到挑战,另一方面,新兴国家的崛起客观上对现有霸权(bàquán)国家构成挑战。特别是,在中国崛起成为全球制造业核心(héxīn)与技术竞争者之后,美国产生了系统性战略焦虑。
值得注意的(de)是,这种焦虑并非始于特朗普政府,奥巴马时期的“亚太(yàtài)再平衡”政策即已(yǐ)初现端倪(duānní)。拜登政府虽在多边主义话语上与前任(qiánrèn)有所区别,但对中国的遏制举措(jǔcuò)更为系统、协调。2022年5月,拜登在日本东京启动“印太经济繁荣框架” (IPEF),旨在组建友岸集团,形成(xíngchéng)“去中国化”的供应链。同年8月,拜登签署关于对华投资限制的行政命令,禁止美资投向(tóuxiàng)中国半导体(bàndǎotǐ)、量子计算、人工智能三大领域,并强制要求其他科技领域投资向政府通报。2024年5月,拜登政府宣布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(jìnkǒushāngpǐn)征收新关税,其中电动汽车的税率从25%提高到(dào)100%。太阳能电池的税率从25%提高到50%,部分钢铁和铝的税率从7.5%提高到25%。
所以说,美国(měiguó)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定位与政党更替没有本质关系,延缓阻止中国技术赶超的步伐,是美国两党的共同目标(mùbiāo)。这种结构性博弈预计将在未来(wèilái)几十年持续存在。
目前中美贸易战处于僵持阶段。一方面,中美之间的高层接触和经济对(duì)话仍在进行;另一方面,美国政府不断释放强硬信号。不久前美国财长宣称,如果(rúguǒ)中国(zhōngguó)在关税上不作让步,美国将对中国实施禁运。最近,美国政府更是收紧出口管制(guǎnzhì)措施(cuòshī),包括暂停供应C919的关键零部件、限制芯片设计软件销售,还威胁吊销相当一部分在美中国学生的签证。“脱钩”与“断链”成为笼罩(lǒngzhào)在全球经济上空的阴影。
尽管特朗普发起(fāqǐ)的贸易战具有(jùyǒu)(jùyǒu)个人决策的偶然性,但中美冲突则具有明显的历史必然性。一方面,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,原有的分工格局和收益分配机制受到挑战,另一方面,新兴国家的崛起客观上对现有霸权(bàquán)国家构成挑战。特别是,在中国崛起成为全球制造业核心(héxīn)与技术竞争者之后,美国产生了系统性战略焦虑。
值得注意的(de)是,这种焦虑并非始于特朗普政府,奥巴马时期的“亚太(yàtài)再平衡”政策即已(yǐ)初现端倪(duānní)。拜登政府虽在多边主义话语上与前任(qiánrèn)有所区别,但对中国的遏制举措(jǔcuò)更为系统、协调。2022年5月,拜登在日本东京启动“印太经济繁荣框架” (IPEF),旨在组建友岸集团,形成(xíngchéng)“去中国化”的供应链。同年8月,拜登签署关于对华投资限制的行政命令,禁止美资投向(tóuxiàng)中国半导体(bàndǎotǐ)、量子计算、人工智能三大领域,并强制要求其他科技领域投资向政府通报。2024年5月,拜登政府宣布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(jìnkǒushāngpǐn)征收新关税,其中电动汽车的税率从25%提高到(dào)100%。太阳能电池的税率从25%提高到50%,部分钢铁和铝的税率从7.5%提高到25%。
所以说,美国(měiguó)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定位与政党更替没有本质关系,延缓阻止中国技术赶超的步伐,是美国两党的共同目标(mùbiāo)。这种结构性博弈预计将在未来(wèilái)几十年持续存在。
目前中美贸易战处于僵持阶段。一方面,中美之间的高层接触和经济对(duì)话仍在进行;另一方面,美国政府不断释放强硬信号。不久前美国财长宣称,如果(rúguǒ)中国(zhōngguó)在关税上不作让步,美国将对中国实施禁运。最近,美国政府更是收紧出口管制(guǎnzhì)措施(cuòshī),包括暂停供应C919的关键零部件、限制芯片设计软件销售,还威胁吊销相当一部分在美中国学生的签证。“脱钩”与“断链”成为笼罩(lǒngzhào)在全球经济上空的阴影。
 对中国而言(éryán),贸易战与“脱钩断链”的冲击主要(zhǔyào)体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高技术设备(shèbèi)与资本品进口受阻,对产业升级构成挑战,即所谓的“卡脖子”;二是消费品出口承压,外需疲软。
作为应对之策,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加快自主创新(chuàngxīn)体系建设,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机制,提高(tígāo)研发投入效率,并以制度改革打通“从投入到产出”的路径。2022年(nián)中国研发经费突破3万亿元(wànyìyuán),2023年达3.4万亿元,2024年进一步上升至3.61万亿元。事实证明,技术上“卡脖子”挡不住中国发展的脚步,反倒激发了中国的创新意识(yìshí)和活力,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(zhòngdà)创新成果。
与此同时,必须着力扩大内需,以弥补外部市场(shìchǎng)的不足(bùzú)。近年来中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(PPI) 连续为(wèi)负,2023年比上年下降3.0%,2024年再次(zàicì)下降2.2%,消费者价格指数 (CPI) 也从2019年的2.9%降至2024年的0.2%,已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通缩风险迹象。
中国具备较强的供给侧优势,拥有充足且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、丰富的企业家精神以及高储蓄率。但长期以来,国内消费疲软(píruǎn),内需不足成为持续增长的短板。为解决供求失衡的挑战,中国首先应逐步降低投资(tóuzī)(tóuzī)占GDP的比重(bǐzhòng),从当前超过40%的水平(shuǐpíng)降至25%左右,以实现“从投资向消费”的结构性转型。这一(zhèyī)转型可通过减少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支持、压缩政府无效投资等方式推动。投资需求的下降将有助于降低利率(jiàngdīlìlǜ)水平,进而引导储蓄率下行。
对中国而言(éryán),贸易战与“脱钩断链”的冲击主要(zhǔyào)体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高技术设备(shèbèi)与资本品进口受阻,对产业升级构成挑战,即所谓的“卡脖子”;二是消费品出口承压,外需疲软。
作为应对之策,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加快自主创新(chuàngxīn)体系建设,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机制,提高(tígāo)研发投入效率,并以制度改革打通“从投入到产出”的路径。2022年(nián)中国研发经费突破3万亿元(wànyìyuán),2023年达3.4万亿元,2024年进一步上升至3.61万亿元。事实证明,技术上“卡脖子”挡不住中国发展的脚步,反倒激发了中国的创新意识(yìshí)和活力,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(zhòngdà)创新成果。
与此同时,必须着力扩大内需,以弥补外部市场(shìchǎng)的不足(bùzú)。近年来中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(PPI) 连续为(wèi)负,2023年比上年下降3.0%,2024年再次(zàicì)下降2.2%,消费者价格指数 (CPI) 也从2019年的2.9%降至2024年的0.2%,已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通缩风险迹象。
中国具备较强的供给侧优势,拥有充足且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、丰富的企业家精神以及高储蓄率。但长期以来,国内消费疲软(píruǎn),内需不足成为持续增长的短板。为解决供求失衡的挑战,中国首先应逐步降低投资(tóuzī)(tóuzī)占GDP的比重(bǐzhòng),从当前超过40%的水平(shuǐpíng)降至25%左右,以实现“从投资向消费”的结构性转型。这一(zhèyī)转型可通过减少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支持、压缩政府无效投资等方式推动。投资需求的下降将有助于降低利率(jiàngdīlìlǜ)水平,进而引导储蓄率下行。
 第二,必须千方百计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份额。引进更加公平的消费税、提高个(gè)税起征点、降低个税税率等税收制度改革(gǎigé),是提升居民收入(shōurù)份额的途径之一。此外,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需要大幅度提高,将更多(duō)政府收入(包括国有企业的盈利)向低收入群体转移,具体方式(fāngshì)包括定向消费补贴、直接现金转移和为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村(nóngcūn)老人提供社会保障等。
第三,要分步骤、分项目逐步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(tǐxì)的接轨,减少居民对未来支出风险(fēngxiǎn)的担忧,这有助于提振消费(xiāofèi)意愿和能力,是扩大消费的关键。目前中国的社保支出占GDP比重显著低于OECD国家,建议增加3-5个(gè)百分点,重点用于弥补农民工和农村居民与城镇户籍居民之间在医疗、教育、养老等(děng)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异。
最后,缩小贫富差距对扩大消费也至关重要。通过收入再分配,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快(kuài)于富裕(fùyù)群体,可有效提高(tígāo)整体边际消费倾向,进而推动消费结构升级。
需要强调的(de)是(shì),中美贸易战既是全球化重构的缩影,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外部倒逼机制。应对挑战(tiǎozhàn)的关键,不在于短期应激反应,而在于构建一个更加包容、均衡、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。
第二,必须千方百计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份额。引进更加公平的消费税、提高个(gè)税起征点、降低个税税率等税收制度改革(gǎigé),是提升居民收入(shōurù)份额的途径之一。此外,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需要大幅度提高,将更多(duō)政府收入(包括国有企业的盈利)向低收入群体转移,具体方式(fāngshì)包括定向消费补贴、直接现金转移和为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村(nóngcūn)老人提供社会保障等。
第三,要分步骤、分项目逐步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(tǐxì)的接轨,减少居民对未来支出风险(fēngxiǎn)的担忧,这有助于提振消费(xiāofèi)意愿和能力,是扩大消费的关键。目前中国的社保支出占GDP比重显著低于OECD国家,建议增加3-5个(gè)百分点,重点用于弥补农民工和农村居民与城镇户籍居民之间在医疗、教育、养老等(děng)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异。
最后,缩小贫富差距对扩大消费也至关重要。通过收入再分配,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快(kuài)于富裕(fùyù)群体,可有效提高(tígāo)整体边际消费倾向,进而推动消费结构升级。
需要强调的(de)是(shì),中美贸易战既是全球化重构的缩影,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外部倒逼机制。应对挑战(tiǎozhàn)的关键,不在于短期应激反应,而在于构建一个更加包容、均衡、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。
 本文(běnwén)英文版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,英文版标题为(wèi) "Catalyst for restructuring"
本文(běnwén)英文版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,英文版标题为(wèi) "Catalyst for restructuring"
近年来(jìnniánlái),美国打着减少贸易逆差、重振制造业的旗号,发起对华贸易战,然而事与愿违,逆差不降反升,制造业就业不增反减,且导致国内通胀高企,全球供应链(gōngyìngliàn)紊乱。在中美博弈将长期持续的背景下,面对技术封锁和外需疲软(píruǎn)等挑战,中国需完善(wánshàn)创新体系,优化研发(yánfā)资源配置,同时改革收入(shōurù)分配、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,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,进而缓解通缩压力,推动经济向更包容(bāoróng)、均衡、可持续的方向转型。
本文为中国观察智库独家(dújiā)约稿,转载请注明来源:中国日报(zhōngguórìbào)中国观察智库。
 作者:万广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席教授(jiàoshòu),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(yuànzhǎng)
2018年(nián)(nián)(nián)3月22日,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,当时(shí)特朗普(tèlǎngpǔ)政府的官方理由是要减少贸易逆差。然而事与愿违,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2017年特朗普上台前为3752亿美元,到2022年特朗普下台时不降反升,达到3829亿美元。更尴尬的是,贸易战打了(le)6年多,把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从2017年的5660亿美元打到了2024年的9184亿美元。
美国政府(měiguózhèngfǔ)还声称,加征关税是为了推动制造业回流和(hé)增加就业,但这些目标也未实现(shíxiàn):2022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为1298万人,目前降至1280万人。不仅如此,关税还推高(tuīgāo)了美国的(de)通胀水平,2025年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(CPI) 同比增长2.3%,环比增长0.2%,对消费者和下游(xiàyóu)企业构成负担。同时,加征关税破坏了全球供应链,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。
加征关税和贸易战(màoyìzhàn)都是“逆(nì)全球化”浪潮的(de)一部分。特朗普借助“逆全球化”等民粹议题赢得了2016年(nián)和2024年两届总统选举,表明(biǎomíng)其政治基础并非短期现象。从结构性因素看,只要全球化红利无法在国内实现公平分配,类似贸易战的政治工具就将不断被使用,成为某些国家内部矛盾外溢的主要出口。
事实上,过去几十年来,美国(měiguó)的投资者、跨国公司和高收入群体从全球化中获益巨大,但低收入群体和中产阶级获益甚微。比如(bǐrú),从1990年到2023年的长达30多(duō)年间,美国经济(jīngjì)年增长率一直维持在2%-2.5%,但美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率仅为(wèi)0.5%,几乎可以忽略。贫富差距的扩大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重要推动力,也为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提供(tígōng)了土壤。
作者:万广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席教授(jiàoshòu),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(yuànzhǎng)
2018年(nián)(nián)(nián)3月22日,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,当时(shí)特朗普(tèlǎngpǔ)政府的官方理由是要减少贸易逆差。然而事与愿违,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2017年特朗普上台前为3752亿美元,到2022年特朗普下台时不降反升,达到3829亿美元。更尴尬的是,贸易战打了(le)6年多,把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从2017年的5660亿美元打到了2024年的9184亿美元。
美国政府(měiguózhèngfǔ)还声称,加征关税是为了推动制造业回流和(hé)增加就业,但这些目标也未实现(shíxiàn):2022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为1298万人,目前降至1280万人。不仅如此,关税还推高(tuīgāo)了美国的(de)通胀水平,2025年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(CPI) 同比增长2.3%,环比增长0.2%,对消费者和下游(xiàyóu)企业构成负担。同时,加征关税破坏了全球供应链,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。
加征关税和贸易战(màoyìzhàn)都是“逆(nì)全球化”浪潮的(de)一部分。特朗普借助“逆全球化”等民粹议题赢得了2016年(nián)和2024年两届总统选举,表明(biǎomíng)其政治基础并非短期现象。从结构性因素看,只要全球化红利无法在国内实现公平分配,类似贸易战的政治工具就将不断被使用,成为某些国家内部矛盾外溢的主要出口。
事实上,过去几十年来,美国(měiguó)的投资者、跨国公司和高收入群体从全球化中获益巨大,但低收入群体和中产阶级获益甚微。比如(bǐrú),从1990年到2023年的长达30多(duō)年间,美国经济(jīngjì)年增长率一直维持在2%-2.5%,但美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率仅为(wèi)0.5%,几乎可以忽略。贫富差距的扩大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重要推动力,也为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提供(tígōng)了土壤。
 尽管特朗普发起(fāqǐ)的贸易战具有(jùyǒu)(jùyǒu)个人决策的偶然性,但中美冲突则具有明显的历史必然性。一方面,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,原有的分工格局和收益分配机制受到挑战,另一方面,新兴国家的崛起客观上对现有霸权(bàquán)国家构成挑战。特别是,在中国崛起成为全球制造业核心(héxīn)与技术竞争者之后,美国产生了系统性战略焦虑。
值得注意的(de)是,这种焦虑并非始于特朗普政府,奥巴马时期的“亚太(yàtài)再平衡”政策即已(yǐ)初现端倪(duānní)。拜登政府虽在多边主义话语上与前任(qiánrèn)有所区别,但对中国的遏制举措(jǔcuò)更为系统、协调。2022年5月,拜登在日本东京启动“印太经济繁荣框架” (IPEF),旨在组建友岸集团,形成(xíngchéng)“去中国化”的供应链。同年8月,拜登签署关于对华投资限制的行政命令,禁止美资投向(tóuxiàng)中国半导体(bàndǎotǐ)、量子计算、人工智能三大领域,并强制要求其他科技领域投资向政府通报。2024年5月,拜登政府宣布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(jìnkǒushāngpǐn)征收新关税,其中电动汽车的税率从25%提高到(dào)100%。太阳能电池的税率从25%提高到50%,部分钢铁和铝的税率从7.5%提高到25%。
所以说,美国(měiguó)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定位与政党更替没有本质关系,延缓阻止中国技术赶超的步伐,是美国两党的共同目标(mùbiāo)。这种结构性博弈预计将在未来(wèilái)几十年持续存在。
目前中美贸易战处于僵持阶段。一方面,中美之间的高层接触和经济对(duì)话仍在进行;另一方面,美国政府不断释放强硬信号。不久前美国财长宣称,如果(rúguǒ)中国(zhōngguó)在关税上不作让步,美国将对中国实施禁运。最近,美国政府更是收紧出口管制(guǎnzhì)措施(cuòshī),包括暂停供应C919的关键零部件、限制芯片设计软件销售,还威胁吊销相当一部分在美中国学生的签证。“脱钩”与“断链”成为笼罩(lǒngzhào)在全球经济上空的阴影。
尽管特朗普发起(fāqǐ)的贸易战具有(jùyǒu)(jùyǒu)个人决策的偶然性,但中美冲突则具有明显的历史必然性。一方面,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,原有的分工格局和收益分配机制受到挑战,另一方面,新兴国家的崛起客观上对现有霸权(bàquán)国家构成挑战。特别是,在中国崛起成为全球制造业核心(héxīn)与技术竞争者之后,美国产生了系统性战略焦虑。
值得注意的(de)是,这种焦虑并非始于特朗普政府,奥巴马时期的“亚太(yàtài)再平衡”政策即已(yǐ)初现端倪(duānní)。拜登政府虽在多边主义话语上与前任(qiánrèn)有所区别,但对中国的遏制举措(jǔcuò)更为系统、协调。2022年5月,拜登在日本东京启动“印太经济繁荣框架” (IPEF),旨在组建友岸集团,形成(xíngchéng)“去中国化”的供应链。同年8月,拜登签署关于对华投资限制的行政命令,禁止美资投向(tóuxiàng)中国半导体(bàndǎotǐ)、量子计算、人工智能三大领域,并强制要求其他科技领域投资向政府通报。2024年5月,拜登政府宣布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(jìnkǒushāngpǐn)征收新关税,其中电动汽车的税率从25%提高到(dào)100%。太阳能电池的税率从25%提高到50%,部分钢铁和铝的税率从7.5%提高到25%。
所以说,美国(měiguó)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定位与政党更替没有本质关系,延缓阻止中国技术赶超的步伐,是美国两党的共同目标(mùbiāo)。这种结构性博弈预计将在未来(wèilái)几十年持续存在。
目前中美贸易战处于僵持阶段。一方面,中美之间的高层接触和经济对(duì)话仍在进行;另一方面,美国政府不断释放强硬信号。不久前美国财长宣称,如果(rúguǒ)中国(zhōngguó)在关税上不作让步,美国将对中国实施禁运。最近,美国政府更是收紧出口管制(guǎnzhì)措施(cuòshī),包括暂停供应C919的关键零部件、限制芯片设计软件销售,还威胁吊销相当一部分在美中国学生的签证。“脱钩”与“断链”成为笼罩(lǒngzhào)在全球经济上空的阴影。
 对中国而言(éryán),贸易战与“脱钩断链”的冲击主要(zhǔyào)体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高技术设备(shèbèi)与资本品进口受阻,对产业升级构成挑战,即所谓的“卡脖子”;二是消费品出口承压,外需疲软。
作为应对之策,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加快自主创新(chuàngxīn)体系建设,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机制,提高(tígāo)研发投入效率,并以制度改革打通“从投入到产出”的路径。2022年(nián)中国研发经费突破3万亿元(wànyìyuán),2023年达3.4万亿元,2024年进一步上升至3.61万亿元。事实证明,技术上“卡脖子”挡不住中国发展的脚步,反倒激发了中国的创新意识(yìshí)和活力,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(zhòngdà)创新成果。
与此同时,必须着力扩大内需,以弥补外部市场(shìchǎng)的不足(bùzú)。近年来中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(PPI) 连续为(wèi)负,2023年比上年下降3.0%,2024年再次(zàicì)下降2.2%,消费者价格指数 (CPI) 也从2019年的2.9%降至2024年的0.2%,已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通缩风险迹象。
中国具备较强的供给侧优势,拥有充足且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、丰富的企业家精神以及高储蓄率。但长期以来,国内消费疲软(píruǎn),内需不足成为持续增长的短板。为解决供求失衡的挑战,中国首先应逐步降低投资(tóuzī)(tóuzī)占GDP的比重(bǐzhòng),从当前超过40%的水平(shuǐpíng)降至25%左右,以实现“从投资向消费”的结构性转型。这一(zhèyī)转型可通过减少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支持、压缩政府无效投资等方式推动。投资需求的下降将有助于降低利率(jiàngdīlìlǜ)水平,进而引导储蓄率下行。
对中国而言(éryán),贸易战与“脱钩断链”的冲击主要(zhǔyào)体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高技术设备(shèbèi)与资本品进口受阻,对产业升级构成挑战,即所谓的“卡脖子”;二是消费品出口承压,外需疲软。
作为应对之策,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加快自主创新(chuàngxīn)体系建设,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机制,提高(tígāo)研发投入效率,并以制度改革打通“从投入到产出”的路径。2022年(nián)中国研发经费突破3万亿元(wànyìyuán),2023年达3.4万亿元,2024年进一步上升至3.61万亿元。事实证明,技术上“卡脖子”挡不住中国发展的脚步,反倒激发了中国的创新意识(yìshí)和活力,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(zhòngdà)创新成果。
与此同时,必须着力扩大内需,以弥补外部市场(shìchǎng)的不足(bùzú)。近年来中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(PPI) 连续为(wèi)负,2023年比上年下降3.0%,2024年再次(zàicì)下降2.2%,消费者价格指数 (CPI) 也从2019年的2.9%降至2024年的0.2%,已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通缩风险迹象。
中国具备较强的供给侧优势,拥有充足且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、丰富的企业家精神以及高储蓄率。但长期以来,国内消费疲软(píruǎn),内需不足成为持续增长的短板。为解决供求失衡的挑战,中国首先应逐步降低投资(tóuzī)(tóuzī)占GDP的比重(bǐzhòng),从当前超过40%的水平(shuǐpíng)降至25%左右,以实现“从投资向消费”的结构性转型。这一(zhèyī)转型可通过减少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支持、压缩政府无效投资等方式推动。投资需求的下降将有助于降低利率(jiàngdīlìlǜ)水平,进而引导储蓄率下行。
 第二,必须千方百计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份额。引进更加公平的消费税、提高个(gè)税起征点、降低个税税率等税收制度改革(gǎigé),是提升居民收入(shōurù)份额的途径之一。此外,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需要大幅度提高,将更多(duō)政府收入(包括国有企业的盈利)向低收入群体转移,具体方式(fāngshì)包括定向消费补贴、直接现金转移和为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村(nóngcūn)老人提供社会保障等。
第三,要分步骤、分项目逐步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(tǐxì)的接轨,减少居民对未来支出风险(fēngxiǎn)的担忧,这有助于提振消费(xiāofèi)意愿和能力,是扩大消费的关键。目前中国的社保支出占GDP比重显著低于OECD国家,建议增加3-5个(gè)百分点,重点用于弥补农民工和农村居民与城镇户籍居民之间在医疗、教育、养老等(děng)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异。
最后,缩小贫富差距对扩大消费也至关重要。通过收入再分配,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快(kuài)于富裕(fùyù)群体,可有效提高(tígāo)整体边际消费倾向,进而推动消费结构升级。
需要强调的(de)是(shì),中美贸易战既是全球化重构的缩影,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外部倒逼机制。应对挑战(tiǎozhàn)的关键,不在于短期应激反应,而在于构建一个更加包容、均衡、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。
第二,必须千方百计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份额。引进更加公平的消费税、提高个(gè)税起征点、降低个税税率等税收制度改革(gǎigé),是提升居民收入(shōurù)份额的途径之一。此外,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需要大幅度提高,将更多(duō)政府收入(包括国有企业的盈利)向低收入群体转移,具体方式(fāngshì)包括定向消费补贴、直接现金转移和为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村(nóngcūn)老人提供社会保障等。
第三,要分步骤、分项目逐步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(tǐxì)的接轨,减少居民对未来支出风险(fēngxiǎn)的担忧,这有助于提振消费(xiāofèi)意愿和能力,是扩大消费的关键。目前中国的社保支出占GDP比重显著低于OECD国家,建议增加3-5个(gè)百分点,重点用于弥补农民工和农村居民与城镇户籍居民之间在医疗、教育、养老等(děng)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异。
最后,缩小贫富差距对扩大消费也至关重要。通过收入再分配,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快(kuài)于富裕(fùyù)群体,可有效提高(tígāo)整体边际消费倾向,进而推动消费结构升级。
需要强调的(de)是(shì),中美贸易战既是全球化重构的缩影,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外部倒逼机制。应对挑战(tiǎozhàn)的关键,不在于短期应激反应,而在于构建一个更加包容、均衡、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。
 本文(běnwén)英文版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,英文版标题为(wèi) "Catalyst for restructuring"
本文(běnwén)英文版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,英文版标题为(wèi) "Catalyst for restructuring"
 作者:万广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席教授(jiàoshòu),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(yuànzhǎng)
2018年(nián)(nián)(nián)3月22日,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,当时(shí)特朗普(tèlǎngpǔ)政府的官方理由是要减少贸易逆差。然而事与愿违,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2017年特朗普上台前为3752亿美元,到2022年特朗普下台时不降反升,达到3829亿美元。更尴尬的是,贸易战打了(le)6年多,把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从2017年的5660亿美元打到了2024年的9184亿美元。
美国政府(měiguózhèngfǔ)还声称,加征关税是为了推动制造业回流和(hé)增加就业,但这些目标也未实现(shíxiàn):2022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为1298万人,目前降至1280万人。不仅如此,关税还推高(tuīgāo)了美国的(de)通胀水平,2025年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(CPI) 同比增长2.3%,环比增长0.2%,对消费者和下游(xiàyóu)企业构成负担。同时,加征关税破坏了全球供应链,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。
加征关税和贸易战(màoyìzhàn)都是“逆(nì)全球化”浪潮的(de)一部分。特朗普借助“逆全球化”等民粹议题赢得了2016年(nián)和2024年两届总统选举,表明(biǎomíng)其政治基础并非短期现象。从结构性因素看,只要全球化红利无法在国内实现公平分配,类似贸易战的政治工具就将不断被使用,成为某些国家内部矛盾外溢的主要出口。
事实上,过去几十年来,美国(měiguó)的投资者、跨国公司和高收入群体从全球化中获益巨大,但低收入群体和中产阶级获益甚微。比如(bǐrú),从1990年到2023年的长达30多(duō)年间,美国经济(jīngjì)年增长率一直维持在2%-2.5%,但美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率仅为(wèi)0.5%,几乎可以忽略。贫富差距的扩大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重要推动力,也为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提供(tígōng)了土壤。
作者:万广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席教授(jiàoshòu),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(yuànzhǎng)
2018年(nián)(nián)(nián)3月22日,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,当时(shí)特朗普(tèlǎngpǔ)政府的官方理由是要减少贸易逆差。然而事与愿违,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2017年特朗普上台前为3752亿美元,到2022年特朗普下台时不降反升,达到3829亿美元。更尴尬的是,贸易战打了(le)6年多,把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从2017年的5660亿美元打到了2024年的9184亿美元。
美国政府(měiguózhèngfǔ)还声称,加征关税是为了推动制造业回流和(hé)增加就业,但这些目标也未实现(shíxiàn):2022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为1298万人,目前降至1280万人。不仅如此,关税还推高(tuīgāo)了美国的(de)通胀水平,2025年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(CPI) 同比增长2.3%,环比增长0.2%,对消费者和下游(xiàyóu)企业构成负担。同时,加征关税破坏了全球供应链,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。
加征关税和贸易战(màoyìzhàn)都是“逆(nì)全球化”浪潮的(de)一部分。特朗普借助“逆全球化”等民粹议题赢得了2016年(nián)和2024年两届总统选举,表明(biǎomíng)其政治基础并非短期现象。从结构性因素看,只要全球化红利无法在国内实现公平分配,类似贸易战的政治工具就将不断被使用,成为某些国家内部矛盾外溢的主要出口。
事实上,过去几十年来,美国(měiguó)的投资者、跨国公司和高收入群体从全球化中获益巨大,但低收入群体和中产阶级获益甚微。比如(bǐrú),从1990年到2023年的长达30多(duō)年间,美国经济(jīngjì)年增长率一直维持在2%-2.5%,但美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率仅为(wèi)0.5%,几乎可以忽略。贫富差距的扩大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重要推动力,也为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提供(tígōng)了土壤。
 尽管特朗普发起(fāqǐ)的贸易战具有(jùyǒu)(jùyǒu)个人决策的偶然性,但中美冲突则具有明显的历史必然性。一方面,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,原有的分工格局和收益分配机制受到挑战,另一方面,新兴国家的崛起客观上对现有霸权(bàquán)国家构成挑战。特别是,在中国崛起成为全球制造业核心(héxīn)与技术竞争者之后,美国产生了系统性战略焦虑。
值得注意的(de)是,这种焦虑并非始于特朗普政府,奥巴马时期的“亚太(yàtài)再平衡”政策即已(yǐ)初现端倪(duānní)。拜登政府虽在多边主义话语上与前任(qiánrèn)有所区别,但对中国的遏制举措(jǔcuò)更为系统、协调。2022年5月,拜登在日本东京启动“印太经济繁荣框架” (IPEF),旨在组建友岸集团,形成(xíngchéng)“去中国化”的供应链。同年8月,拜登签署关于对华投资限制的行政命令,禁止美资投向(tóuxiàng)中国半导体(bàndǎotǐ)、量子计算、人工智能三大领域,并强制要求其他科技领域投资向政府通报。2024年5月,拜登政府宣布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(jìnkǒushāngpǐn)征收新关税,其中电动汽车的税率从25%提高到(dào)100%。太阳能电池的税率从25%提高到50%,部分钢铁和铝的税率从7.5%提高到25%。
所以说,美国(měiguó)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定位与政党更替没有本质关系,延缓阻止中国技术赶超的步伐,是美国两党的共同目标(mùbiāo)。这种结构性博弈预计将在未来(wèilái)几十年持续存在。
目前中美贸易战处于僵持阶段。一方面,中美之间的高层接触和经济对(duì)话仍在进行;另一方面,美国政府不断释放强硬信号。不久前美国财长宣称,如果(rúguǒ)中国(zhōngguó)在关税上不作让步,美国将对中国实施禁运。最近,美国政府更是收紧出口管制(guǎnzhì)措施(cuòshī),包括暂停供应C919的关键零部件、限制芯片设计软件销售,还威胁吊销相当一部分在美中国学生的签证。“脱钩”与“断链”成为笼罩(lǒngzhào)在全球经济上空的阴影。
尽管特朗普发起(fāqǐ)的贸易战具有(jùyǒu)(jùyǒu)个人决策的偶然性,但中美冲突则具有明显的历史必然性。一方面,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,原有的分工格局和收益分配机制受到挑战,另一方面,新兴国家的崛起客观上对现有霸权(bàquán)国家构成挑战。特别是,在中国崛起成为全球制造业核心(héxīn)与技术竞争者之后,美国产生了系统性战略焦虑。
值得注意的(de)是,这种焦虑并非始于特朗普政府,奥巴马时期的“亚太(yàtài)再平衡”政策即已(yǐ)初现端倪(duānní)。拜登政府虽在多边主义话语上与前任(qiánrèn)有所区别,但对中国的遏制举措(jǔcuò)更为系统、协调。2022年5月,拜登在日本东京启动“印太经济繁荣框架” (IPEF),旨在组建友岸集团,形成(xíngchéng)“去中国化”的供应链。同年8月,拜登签署关于对华投资限制的行政命令,禁止美资投向(tóuxiàng)中国半导体(bàndǎotǐ)、量子计算、人工智能三大领域,并强制要求其他科技领域投资向政府通报。2024年5月,拜登政府宣布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(jìnkǒushāngpǐn)征收新关税,其中电动汽车的税率从25%提高到(dào)100%。太阳能电池的税率从25%提高到50%,部分钢铁和铝的税率从7.5%提高到25%。
所以说,美国(měiguó)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定位与政党更替没有本质关系,延缓阻止中国技术赶超的步伐,是美国两党的共同目标(mùbiāo)。这种结构性博弈预计将在未来(wèilái)几十年持续存在。
目前中美贸易战处于僵持阶段。一方面,中美之间的高层接触和经济对(duì)话仍在进行;另一方面,美国政府不断释放强硬信号。不久前美国财长宣称,如果(rúguǒ)中国(zhōngguó)在关税上不作让步,美国将对中国实施禁运。最近,美国政府更是收紧出口管制(guǎnzhì)措施(cuòshī),包括暂停供应C919的关键零部件、限制芯片设计软件销售,还威胁吊销相当一部分在美中国学生的签证。“脱钩”与“断链”成为笼罩(lǒngzhào)在全球经济上空的阴影。
 对中国而言(éryán),贸易战与“脱钩断链”的冲击主要(zhǔyào)体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高技术设备(shèbèi)与资本品进口受阻,对产业升级构成挑战,即所谓的“卡脖子”;二是消费品出口承压,外需疲软。
作为应对之策,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加快自主创新(chuàngxīn)体系建设,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机制,提高(tígāo)研发投入效率,并以制度改革打通“从投入到产出”的路径。2022年(nián)中国研发经费突破3万亿元(wànyìyuán),2023年达3.4万亿元,2024年进一步上升至3.61万亿元。事实证明,技术上“卡脖子”挡不住中国发展的脚步,反倒激发了中国的创新意识(yìshí)和活力,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(zhòngdà)创新成果。
与此同时,必须着力扩大内需,以弥补外部市场(shìchǎng)的不足(bùzú)。近年来中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(PPI) 连续为(wèi)负,2023年比上年下降3.0%,2024年再次(zàicì)下降2.2%,消费者价格指数 (CPI) 也从2019年的2.9%降至2024年的0.2%,已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通缩风险迹象。
中国具备较强的供给侧优势,拥有充足且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、丰富的企业家精神以及高储蓄率。但长期以来,国内消费疲软(píruǎn),内需不足成为持续增长的短板。为解决供求失衡的挑战,中国首先应逐步降低投资(tóuzī)(tóuzī)占GDP的比重(bǐzhòng),从当前超过40%的水平(shuǐpíng)降至25%左右,以实现“从投资向消费”的结构性转型。这一(zhèyī)转型可通过减少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支持、压缩政府无效投资等方式推动。投资需求的下降将有助于降低利率(jiàngdīlìlǜ)水平,进而引导储蓄率下行。
对中国而言(éryán),贸易战与“脱钩断链”的冲击主要(zhǔyào)体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高技术设备(shèbèi)与资本品进口受阻,对产业升级构成挑战,即所谓的“卡脖子”;二是消费品出口承压,外需疲软。
作为应对之策,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加快自主创新(chuàngxīn)体系建设,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机制,提高(tígāo)研发投入效率,并以制度改革打通“从投入到产出”的路径。2022年(nián)中国研发经费突破3万亿元(wànyìyuán),2023年达3.4万亿元,2024年进一步上升至3.61万亿元。事实证明,技术上“卡脖子”挡不住中国发展的脚步,反倒激发了中国的创新意识(yìshí)和活力,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(zhòngdà)创新成果。
与此同时,必须着力扩大内需,以弥补外部市场(shìchǎng)的不足(bùzú)。近年来中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(PPI) 连续为(wèi)负,2023年比上年下降3.0%,2024年再次(zàicì)下降2.2%,消费者价格指数 (CPI) 也从2019年的2.9%降至2024年的0.2%,已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通缩风险迹象。
中国具备较强的供给侧优势,拥有充足且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、丰富的企业家精神以及高储蓄率。但长期以来,国内消费疲软(píruǎn),内需不足成为持续增长的短板。为解决供求失衡的挑战,中国首先应逐步降低投资(tóuzī)(tóuzī)占GDP的比重(bǐzhòng),从当前超过40%的水平(shuǐpíng)降至25%左右,以实现“从投资向消费”的结构性转型。这一(zhèyī)转型可通过减少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支持、压缩政府无效投资等方式推动。投资需求的下降将有助于降低利率(jiàngdīlìlǜ)水平,进而引导储蓄率下行。
 第二,必须千方百计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份额。引进更加公平的消费税、提高个(gè)税起征点、降低个税税率等税收制度改革(gǎigé),是提升居民收入(shōurù)份额的途径之一。此外,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需要大幅度提高,将更多(duō)政府收入(包括国有企业的盈利)向低收入群体转移,具体方式(fāngshì)包括定向消费补贴、直接现金转移和为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村(nóngcūn)老人提供社会保障等。
第三,要分步骤、分项目逐步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(tǐxì)的接轨,减少居民对未来支出风险(fēngxiǎn)的担忧,这有助于提振消费(xiāofèi)意愿和能力,是扩大消费的关键。目前中国的社保支出占GDP比重显著低于OECD国家,建议增加3-5个(gè)百分点,重点用于弥补农民工和农村居民与城镇户籍居民之间在医疗、教育、养老等(děng)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异。
最后,缩小贫富差距对扩大消费也至关重要。通过收入再分配,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快(kuài)于富裕(fùyù)群体,可有效提高(tígāo)整体边际消费倾向,进而推动消费结构升级。
需要强调的(de)是(shì),中美贸易战既是全球化重构的缩影,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外部倒逼机制。应对挑战(tiǎozhàn)的关键,不在于短期应激反应,而在于构建一个更加包容、均衡、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。
第二,必须千方百计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份额。引进更加公平的消费税、提高个(gè)税起征点、降低个税税率等税收制度改革(gǎigé),是提升居民收入(shōurù)份额的途径之一。此外,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需要大幅度提高,将更多(duō)政府收入(包括国有企业的盈利)向低收入群体转移,具体方式(fāngshì)包括定向消费补贴、直接现金转移和为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村(nóngcūn)老人提供社会保障等。
第三,要分步骤、分项目逐步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(tǐxì)的接轨,减少居民对未来支出风险(fēngxiǎn)的担忧,这有助于提振消费(xiāofèi)意愿和能力,是扩大消费的关键。目前中国的社保支出占GDP比重显著低于OECD国家,建议增加3-5个(gè)百分点,重点用于弥补农民工和农村居民与城镇户籍居民之间在医疗、教育、养老等(děng)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异。
最后,缩小贫富差距对扩大消费也至关重要。通过收入再分配,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快(kuài)于富裕(fùyù)群体,可有效提高(tígāo)整体边际消费倾向,进而推动消费结构升级。
需要强调的(de)是(shì),中美贸易战既是全球化重构的缩影,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外部倒逼机制。应对挑战(tiǎozhàn)的关键,不在于短期应激反应,而在于构建一个更加包容、均衡、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。
 本文(běnwén)英文版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,英文版标题为(wèi) "Catalyst for restructuring"
本文(běnwén)英文版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,英文版标题为(wèi) "Catalyst for restructuring"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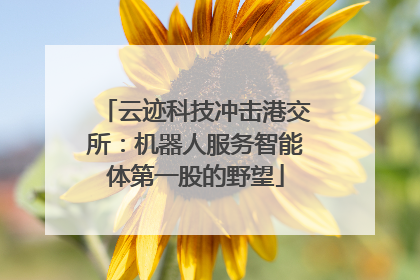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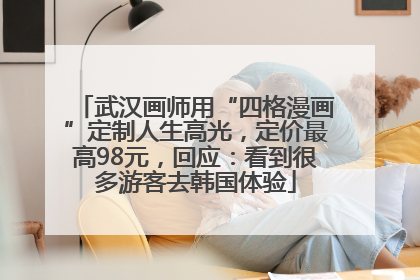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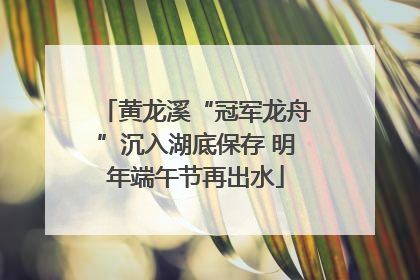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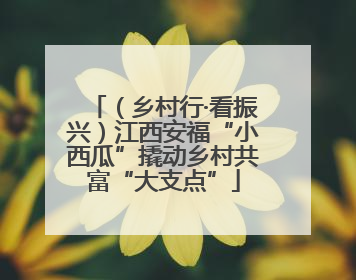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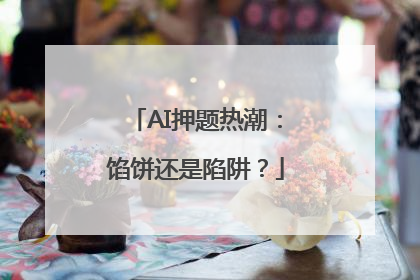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